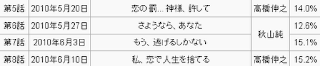Robert Forster有山崎努feel﹐可解饑渴之苦
看了《繼承大丈夫》﹐想起幾部電影:Sofia Coppola的Somewhere﹐宮崎吾朗的《紅花板上的海》﹐以至奇雲高士拿的Dances with Wolves。
想起Sowewhere﹐因為都很hea﹐百無聊賴﹐吹吹海風﹐飲杯野﹐若有若無的異國情調﹐聽聽夏威夷風音樂﹐疑似公路電影之類。
不同的是﹐Sofia那部完全係無故事(條女上堂踩冰﹐長鐘頭拍足五分鐘之類)﹐係「不知所云」的﹐但特別的是﹐全片看畢﹐片子又相當完整地呈現了作者的世界觀﹐佢就係咁無聊﹐但虛無中有真情﹐觀眾可以調侃佢幼稚﹐但不能罵佢膚淺﹐因為佢已相當強烈地將自己僅有的思想﹐通過複雜的藝術手法流露﹐一字記之曰Speechlessness。
小弟可以說﹐Somewher並無驚天動地的事情發生 ,但所有兩父女應該發生的事﹐其實都發生了。《繼承大丈夫》則不一樣﹐有很多峰迴路轉的事情發生﹐但所有一家人應該發生的事﹐其實都沒有發生。
作者機關算盡﹐片子像坐過山車﹐過了一關又一關﹐有點像特區的現狀﹐不斷有各種各樣的喧嘩與危機發生﹐過兩日又忘記了(誰還記得癲狗寶島涉嫌打人什麼的鳥事?)。
《繼承大丈夫》就係有沒完沒了的人和事﹐以一件事cover另一件事﹐末了觀眾什麼都忘記了﹐只記得結局三父女坐埋食雪糕﹐睇電視﹐零點零一公分的反諷都沒有﹐一切家族崩壞的危機﹐輕舟已過﹐又是天朗氣晴的新一天了。
《繼》發生了很多危機﹐老婆昏迷﹐以細女反叛逃避之;細女反叛﹐以大女反叛逃避之;大女反叛﹐以發現老婆勾佬逃避之;老婆勾佬﹐以向老婆情夫尋仇避避之;向老婆情夫尋仇﹐以狂嘴情夫老婆逃避之。在心理學言﹐這是轉移作用(displacement)﹐杮子揀軟的捏﹐末了就是陳冠中的老話:什麼都沒有發生(一開始就說的賣地﹐結果都沒賣)。
一言以蔽之﹐《繼承大丈夫》就是一場cover-up﹐以分散注意﹐來忘記自己的罪。George Clooney對生死問題(安樂死)、夫婦問題(戀人背叛、責任)、父女問題﹐人與自然關係這些問題﹐沒有一絲一毫反省﹐他提倡的﹐只是讓觀眾自我感覺良好的逃避主義﹐讓麻甩佬繼續麻甩的飛機主義(片中有條女經常赤身露體走來走去﹐不外是金魚佬式滿足)。

《繼承大丈夫》與卡通《紅花板上的海》相似的地方﹐是所謂「保育問題」。
《紅》呈現為鄉下學生央求某商事社長﹐保留校園內的一幢舊建築;《繼》則是George Clooney末了拒絕賣地﹐保存了原居民的自然風景。
一無二致的是﹐這兩片「風景」﹐都因為一個有極大權力的人﹐心血來潮的sentiment﹐就被皇恩大赦地保留下來。一言而為天下法﹐這種解決問題的手段﹐不太毛主席一點了嗎? 假若觀眾稍有一點成人的世故﹐不覺得太兒戲、太幼稚一點了嗎?
例如林鄭月娥﹐會因為80後青年絕食﹐就不拆皇后碼頭嗎? 例如鄭汝樺﹐會因為有人圍立法會幾日﹐就推動罷起高鐵﹐將土地還給菜園村居民嗎? 拜託﹐這是2011年﹐是無惡不作的資本主義末世﹐是老美發窮惡四圍咬人的時候﹐是中共蛻變為法西斯的前夕﹐世事沒那麼天真可愛的吧﹐粵語殘片講句﹐大o既唔食(Clooney)﹐細o既都要食架。
好笑的是﹐片子根本唔敢面對這個問題: 老表叫George Clooney向股東演講﹐說明拒絕賣地原委﹐鏡頭close-up Clooney背脊半身﹐即刻溶接﹐返番Clooney 屋企﹐接下一場戲。作者根本解唔通﹐沒什麼﹐佢就係當觀眾係失憶和retarded的 (片子用語﹐絕無貶意)。

最後﹐是Dances with Wolves﹐這觸及《繼承大丈夫》的潛文本﹐美帝國主義者搶掠夏威夷土著土地的醜惡歷史。
《繼承大丈夫》處理這回事﹐是glorify的(手搖鏡遍照牆上的黑白祖先遺照)﹐氣氛莊嚴﹐而末了Clooney體恤民情、抓緊回憶(細女話未同媽媽去過那裡露營)、在全球金融崩壞前名嫌錢腥﹐更是大仁大義。
這就是《繼》偽善之處:Dances with Wolves向印地安人謝罪﹐即使矯揉造作﹐但明刀明槍﹐不失其光明磊落;《繼承大丈夫》借夏威夷佬過橋﹐明明將人家地方搞到面目全非(可對照尤敏片《香港東京夏威夷》﹐就知時光幻變)、非驢非馬﹐然後帶隊crew來獵奇一番﹐你重好意思假仁假義。
《繼承大丈夫》﹐過繼的﹐是美帝國主義者的滔天罪孽吧﹐我繼你個鳥丈夫﹗